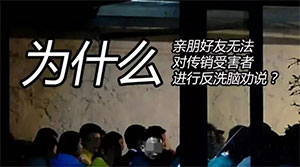我是反传销孟然老师,经常接到从传销逃跑人员的吐槽电话,今天又接到了一个成功逃脱人员的电话:小李是河北工业大学的,大三的时候为了帮一个网友的忙,去了成都,被骗进了传销。当时是蒙着眼睛被送进了一个屋子,所有的私人物品全部被锁在了一个柜子里,每天就在里面上所谓的课程。里面的分工很明确,而且采取的是互相监督的管理模式,比如A、B互为一组,A若逃跑,连带着B往死里打。当时他去了没三天,就看到被抓回来一个,那画面残酷的不忍直视。
我很快的意识到必须有一个严密的计划,而这第一步就是:取得信任。先开始的时候准备趁机逃跑,但发现根本连出门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开始改变策略,决心培养一个让管理者分心习惯:每天凌晨吸烟。首先要让组织者觉得自己已经被洗脑了,洗的很彻底。于是我一跃成为了小组长,这大约花了两星期;然后,再进行反洗脑,慢慢的拥有了一定的说话权。这时我利用说话权来植入一些自己设计好的课程,让组织者慢慢的更信任我。话说,一般人很容易被洗脑,是因为里面很多关于金融学且偷换概念的东西,而我因为专业原因,能够一眼看穿然后举一反三的去骗别人。
这时组织者——这个房间的老大已经和我称兄道弟了,于是我得到了一盒烟。我们睡的是大通铺。第一天晚上凌晨的时候,尝试性的起床上完厕所之后非常轻非常轻地点燃一根烟,并没有人在意;第二天继续,也并没有;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;到了一盒烟快抽完的时候,我走向大门,借着火光看了看锁的构造,发现那是一种非常老式的铁门,无论怎样推开都会发出不小的声音,更枉论安静的夜晚。我不死心的还是试着推了推,火光之下,似乎在睡梦中有人翻了个身。果不其然,第二天,被举报了不知道举报的是谁,但是他们的规定说如果发现有人有逃跑倾向而不举报的话,是要连坐的。大老板知道我很聪明,所以他的信任一直给予在理智范围之内,而这一次,我的行为无异挑战了他的底线。我面不改色的把所有嫌疑全部推到了举报人身上:是他看错了,我每天都会在那抽烟,没事推那铁门干嘛,我还准备多拉点下线多赚点钱呢!
大老板最终决定半信任我,但看管却越发严格起来,除了B,又派出了C。
C是一个小姑娘,年纪不大,性格比较老实。有一天她偷偷找机会拉着我的袖子轻轻说道:你要逃,可不可以带我一起走?我是个很仗义的人,但当时并没有答应,沉默着。我怕了,怕背叛,怕这个姑娘承受不住,会被发现,会拖累更多人连坐。C白天的时候跟着我,B哪怕是上厕所的时候都寸步不离,我走的步步惊心。我开始改变策略,想方设法的弄到了自己的包,拿出了几样东西。到这个时候,前期培训洗脑已经完成,要开始发展下线了。据他们洗脑教育,不久之后自己都会身价过亿,受到万人敬仰,家产成倍增长。所有洗脑成功的人都会做起黄梁梦,所以上家并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度。他们被发了手机,开始联系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当然,每一个电话,每一个短信,都是在严格的被监控状态。这时候我想起一个发小,从小一起长大,我们之间有一些特定的暗号和信息交流方式。他接到了我的危险信号短信。我用暗号表示:我被骗到东莞某个传销组织了,并不知道组织具体位置,且无人生自由。又过了几个星期,到了收获的季节,这批传销组织的人开始收线。组里面有把妹妹骗过来的,有把老友骗过来的,甚至有一个把妈妈骗过来的…不过对他们来说,或许这也不是骗,因为洗脑后的他们觉得这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,赚大钱的机会。
我也随大流让发小赶快来,并且让他扎扎实实打了大几千在卡上。这无疑一箭双雕:通过取款地址可以大致判断出区域。但我这点还是低估了,这个组织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蠢,他们是把卡邮寄到远离此地的地方,找了个第三方取的款,果然老奸巨猾。但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,而本着做事得留后手的原则, 开始布置第二条线——继续保持忠诚度,争取外派。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我表现的很投入,组织者更加欣赏我,监管也松了些,上大号的时候也没有人守着了,有一天,我使了个招把手机偷出来,想着给发小发个确认短信、再给父母报个平安,更冒险的,报个警,拼了。没想到也就是在这天,大头目找我谈话,说自己很欣赏我的能力,已经看作半个自己人了,所以想把我作为骨干,去让更大的boss审核,通过的话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窝点的负责人。我做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表忠心,当时碰那个铁门一顿毒打肯定少不了,这个领导也的确是保了我。我也生出了一些愧疚,如果我真的逃跑了,这个小boss下场肯定不会好看。但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偷偷把手机放了回去,决定背水一战。期间那个女孩又找了我一次。可以想象到这个女孩冒了多大的风险,我已经是头目那边的红人了,如果我举报,下场必定很惨;但也有可能女孩是探子,若是同意,我下场也必定很惨。在这场战争中朋友分不清敌我,所以只能一致对外。我跟那个女孩说:“你这次这样说,我当作没听懂,但是如果有下次,我不会再视而不见,你看清我的立场在想好说什么话。”之后那女孩目光躲闪,也不知想了些什么。
然后,外出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共三个人,一个小组长前面带路,剩下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朋友往前走,我还被蒙上了眼睛下了楼梯,然后走过一个人很少的小巷子,七拐八拐的,等到摘了眼罩的时候,已经来到一个外面的小区了。那是个很老旧的小区,我们走向了中心花园,在正中央有一个很大、有些残破的圆形花坛,因为无人打理里面长满了杂草。花坛外围附带着一圈水泥台子,上面零零星星的环坐着些带着孙子的老太太或者晨练的大爷,感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。当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禁闭时,突然看到第一个人间景观,在心底的印象必然是极尊贵的。我心中涌现出重见天日的快感,也更坚定了逃跑的决心,哪怕付出代价。出了小区,我被塞进了一辆车,又被蒙上了眼睛。我开始记路,先开始向东经过了一个菜市场,又往南转,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坑坑洼洼的巷子。穿梭来,穿梭去,慢慢的开始混淆了,到最后被迫放弃。不过就是这样,也得到了很多的信息:这个窝点在城市的东北角的偏僻的民房里,门前一条路不能开车,和一个老旧有大花园的小区隔得很近,大约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个菜场或者早市,十几分钟的时候有一条很长的烂尾路…我感觉基本上已经可以定位出来这个地方了。到了大boss的地方,依旧是蒙着眼睛上楼,差不多的格局,里面也有一批正在培训的人。大boss接见了他,和他聊了聊。我把逃跑的念头隐藏的非常好。大Boss觉得我可以用,最后非常愉快的送走了我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,送我来的那三个人明显轻松了下来,已经有点把我当自己人看的意思,而且因为大boss看中的人肯定会给一个不错的职位,三个人明显更客气了些。
我以为终于可以不蒙眼睛了,其实并没有。我依旧被蒙着眼睛塞进车里。没想到那司机把车开一半,说是自己家里有点私事,让我们自己回,然后把车停在了公交站。其实组织本身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发生的,可能我的伪装太好,包括司机都明显放松了警惕,也并没有那么在意起来。我们四人在公交车站下车,我也终于被拿掉了眼罩,但是左右两个壮汉依旧形影不离的跟随。为小组长去看公交牌了,我趁乱开始左顾右盼,结果这一下把那几个人搞得警觉了起来——他们真的应该非常紧张,连坐这件事太可怕了。两个壮汉把这事告诉了探路回来的小组长,他们几个人没有原来那么放松了。没一会儿,公交来了。他们一前一后的把我带上了车,因为没有座位,大家站着,拉着头顶的扶手。朋友那时测算,大约离后门有七八米的距离,车里人还不少。重回人类社会,我一瞬间掠过几个想法:
1,当场喊叫,表示自己被传销组织绑架;
2,直接踹倒两个,看机会逃跑;
3,保持不动,走最稳妥的第二方案,等待发小的救援。如果当场喊叫的话,没有朝阳群众的在场,或者那几个人异口同声的表示“此人是精神病”,那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,太简单粗暴了,而且如果被抓回去,有没有命另算;如果直接踹倒两个再看机会跑的话,我通过心算估略出,以自己的最快速度每秒7米,在加上障碍物,自己一秒跑下车的概率只有50%,如果在这1、2秒之内他们反映过来并追下了车,被抓回来就是按逃跑未遂处置,有没有命依旧另算;如果是保持不动,肯定最稳妥,但是重见天日简直遥遥无期。怎么着都很被动,怎么选都有风险,但是这次我压上的是自己的命。当车停稳后,我发现自己还是不敢,放弃吧,放弃吧。也许真的是上天有眼,这一站下的人特别多,我突然福至心灵,假装自己不胜人流的推动,往车门那边又移动了一两米,那三个人立刻警觉了起来。车门关上了,那三人基本已经发现了我的意图,开始以最严密的姿态针对我。这将是一场硬仗,拼的是利用价值和信任程度,而自己胜利的可能,不到两成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站位是这样的:我在中间扶着柱子,左右各有一个壮汉护着,小组长在靠门的这边,也就是说,我三面被包围着。我有些心灰意冷。这个时候,车到站了。小组长旁边的座位上有个老奶奶要下车,嫌组长的站位碍事了,让他让让,组长往旁边站了站。这时候我离门五米。我突然脑袋一热。3,2,1。当门还有一秒钟要关的时候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之势飞奔了出去,把老奶奶撞了一下,而门,关住。每秒7米,而离门5米,我做到了!我没了命一样的向前飞奔,期间回头看过一次,车子不远处停了下来,那三个壮汉离我大概几百米的距离,并且看到了我,向这边奔过来…..我想,我的一生就赌在这上面了,赌输了这条命就没有了,就算还在,整天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小房子里又有什么意义?我飞奔,飞奔,飞奔。似乎把这辈子能跑的步都跑完了。哪里疼都不重要,命还在,他们还没追上这件事就可以代表全世界的幸福,我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,瘫坐在地上,心里想着,如果这样还被抓住,那也就认了吧但他们没有追上来。我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,用口袋里的一点钱坐上了一辆公交车。
小李是幸运的,也是悲哀的,幸运的是他逃脱了传销人员的控制,没有被洗脑,悲哀的是小李这辈子有可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,不过这对小李来说也是一种成长。真爱生命,远离传销,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
本文由:反传销救助中心: 孟然老师 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