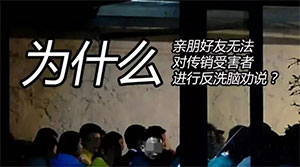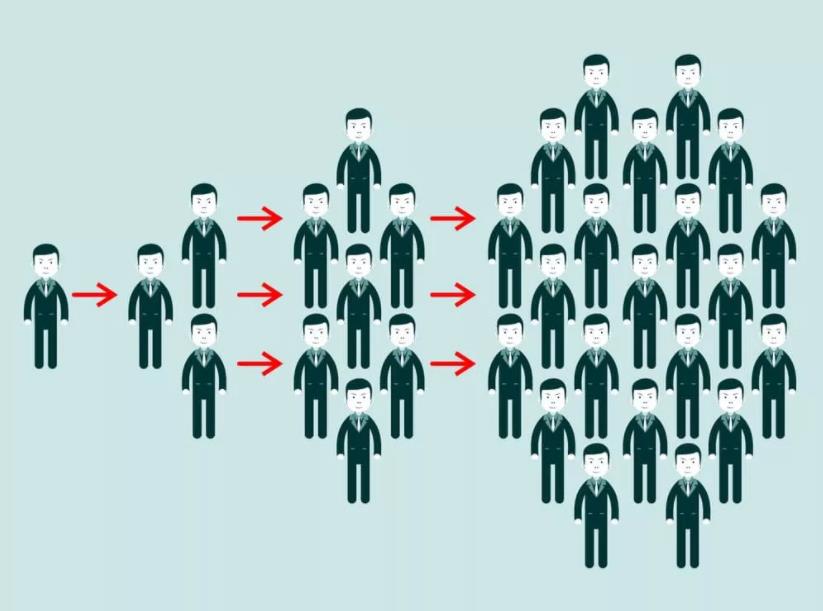
-01-
「老乡见老乡」
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,我在辽宁鞍山开了一家豆腐坊,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,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我想赚钱,想在异乡出人头地,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直到 2004 年的一天,我的小舅子找上了我。他说自己有亲戚在徐州包了水利工程,喊我一起去赚大钱。我没怎么怀疑,就相信了。
2004 年 4 月 19 日,我抵达了徐州。一到那边,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小舅子他们几个的变化都很大,西装革履的,谈吐也不一样了。
第二天早上,他们说工地上出事了,这两天安全检查,他们都没活干,要带我出去转转。当时,一起去的除了小舅子,还有他们公司的几个年轻人。他们一行人把我带到了郊区,说是去参加一个朋友搞的「联欢会」。
「联欢会」的会场里坐满了人,好不热闹。我一到场,他们就要求我上台做自我介绍,还起哄,喊着口号,让我唱首歌。当时的气氛很奇怪,过分热闹,也过分亲热。我没推脱掉,只好唱了首《老乡见老乡》。一曲唱罢,我不由自主地「两眼泪汪汪」,想起了十年未回的家乡,也不禁感念他们这些「老乡」的热情招待。
唱完歌后,我刚一坐下,一位领导派头的人就上台了。他宣布,「今天早会到此结束,生意介绍会马上开始。」
我立刻反应了过来:这
是不是传销?
-02-
洗脑,只需三天
对传销这回事,我其实很敏感。1998 年那会儿,我的堂弟、堂弟媳、堂姐、堂姐夫这一家子都去了湖南郴州搞传销。不仅如此,我在鞍山的时候,也没少听说当地传销组织的活动。
但是,警觉的那一刻,我没有立即离开,反而有点好奇,想看看他们这帮人是怎么骗人的。于是,我坐在台下,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宣讲。
宣讲中,他们的话术很直白,主要围绕着这个行业怎么赚钱的,而其他传统行业赚钱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他们还声称,自己做的是一种国家引进的新型行业,是「21 世纪中国老百姓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」,说什么,「上午拍拍手,下午握握手,钱儿就到手」。
宣讲会结束后,我告诫几个同去的人不要做这个东西,「这就是传销」。但他们否认了我的说法,说自己只是来玩的,过两天工地就开工了。
接下来的两三天,他们又安排我参加了各种集体活动。我很反感,却又碍于面子,不好意思太早离开。
第三天下午,他们告诉我,「上面」下来了几个领导,要请我去酒店吃饭。我竟有点受宠若惊,就跟着他们一块去了。到了以后,我才发现,这根本不是什么饭局,而是又一个分享会。
但是,这一次的分享会和之前都不一样。现场有好几百人,掌声雷动,无比狂热。台上有三个「大领导」,穿金戴银,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。据说,他们是「B 级领导」,「吃宾馆,住宾馆,一个月上万的工资」。
会上,他们三个声情并茂地回忆自己过去在传统行业如何历经艰辛,如何遭人白眼。他们声称,自己到这个「行业」来考察之后,一开始也不认可,也以为是传销;但是,经过几天的考察,他们的疑虑全都打消了。
听完他们的经历之后,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,他们几个看上去谈吐和气质都特别好,令我隐隐心生向往。再加上其中的一个以前做包工头的人还是我的老乡,我难免多信了几分。
分享会上,他们还极力撇清了自己和「传销」的区别——传销是「金字塔架构」,我们是「等腰梯形制」;传销是无限制发展下线,我们只找两到三个「合作伙伴」就可以了;传销一般会控制人身自由,而我们今天则是「来去自由」,没有人会控制你。
说来也奇怪,「被洗脑」这种事好像只发生在一念之间。那场分享会之后,我真心实意地相信,自己遇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哪怕赚不了他们说的几千万,赚个上百万也是不错的。
-03-
我变成了一个去给别人洗脑的人
传销组织内部讲究的是「五级三晋制」,「五级」,指的是业务员分为 A、B、C、D、E 五个级别;「三晋」,指的是从实习业务员到高级业务员之间的三个晋升阶段。
加入组织后,我交了一万多元,成为了一名初级业务员。那个时候,我相信,凭着多年来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经验,自己一定能有机会晋升到 B 级别。而想要晋升,我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拉人头,发展下线。
很多人对我们这些做过传销的有个误解,以为我们明知道是传销,却还去骗人、拉人头。但实际上,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状态——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传销,也不认为自己在害人。我们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是一种利国利民利己的事业,能解决就业,增加税收,抵制外货。
我最先发展的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。我告诉她们,我在这边包了工程,需要人来做饭、打下手,就这么顺利地把她们骗了过来。
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当年 6 月,我就升级到了 C 级别,就自己租了一套房子,成为了一个「寝室长」。
当了「领导」之后,我对这里更有归属感了。在这个地方,「领导」的威信是很高的。比方说,我一回到寝室,所有的业务员都会对我 90 度鞠躬问好;每天起床后,他们都会帮我准备好牙膏和洗脸水;吃饭的时候,我有领导专属的位子,其他业务员碰都不能碰一下。这种氛围给我带来了一种极大的「被尊重」的感觉。
与此同时,我也慢慢看到了行业里残酷的一面。
举个例子吧。有一次,我的寝室来了一对来自云南的小夫妻。他们家里很穷,祖孙三代都是弹棉花的。当时,为了拉他们入伙,我给他们讲了传销话术中经典的「放羊娃的故事」。这个故事是说,有一次,《焦点访谈》的主持人敬一丹到山西去采访一个放羊娃,他们家祖孙三代都在放羊。
敬一丹问他,「你放羊以后要干嘛?」
放羊娃说,「我放完羊以后,就把羊卖了。」
「羊卖了以后呢?」
「我去娶个老婆,给我生娃。」
「生娃以后呢?」
「再给我放羊。」
讲完这个故事,我告诉他们,你们要学会转变观念,否则,祖孙三代都会继续穷下去,继续一代又一代地弹棉花。只要抓住机遇,从此以后,这个行业就能改变你们家族的命运。
于是,夫妻俩掏了一万多块钱,加入了我们。不久后,他们决定先拉家里的姐夫入伙。可是,他们的姐夫不仅对我们的事业很抵触,还要报警。最终,他带走了那位丈夫,女方则被我们想办法留了下来。
男方走了之后,我们便继续给女方洗脑,让她坚定自己的想法,「等到成功了以后,你的家人自然会理解」。
可是,不久之后,她丈夫就回来了,还带了很多亲戚,威胁着要动武。当时,我人在外面,只能给业务员打电话,让他们不要闹大,放这一家人离开。
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的。他们家里本来就不宽裕,一两万块钱的损失足以使他们的家庭雪上加霜。我慢慢意识到,这个行业带来了非常多像他们这样的受害者。
-04-
一桶凉水浇到了我发热的大脑上
在这个行业里做了一年多,我越来越起疑,隐隐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很多问题的。最可疑的是,那些高级别的领导们统统「神龙见首不见尾」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,更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赚到钱。
当时,我小舅子的表哥已经升到了「B 级别」,即便如此,我也依然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,每次见面交钱,也都是偷偷摸摸,鬼鬼祟祟。
2005 年 9 月,就在我加入组织一年多之后,国务院颁布了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。这两部条例第一次在法规上对「传销」做出了界定。
我是通过其他亲人得知这个消息的。当时,他们打电话告诉我,说是在新闻上看到,「你做的那个行业立法了」。我一听,喜出望外,立刻就去了网吧,查阅相关的新闻。
可是,查完这两部条例,我仿佛被一桶凉水浇了个透湿——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符合条例对「传销」的界定。
冷静下来后,我下定了决心:不能再做下去了,这是害人害己的事情。
于是,我找到了小舅子的那位表哥,把他约到一个公园,把我掌握的信息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。我还带他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和新闻,让他认识到,行业里的很多「大佬」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。
小舅子的表哥很纠结,毕竟,他已经做到很高的层级了。但我提醒他,哪怕离开这个行业,凭借他过往的经验和人脉,他在传统行业也一样能做的很好。更重要的是,当时,他的儿子已经考上了我们老家的一个重点中学,还计划日后考军校,「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,一旦你出事了,你的儿子政审就过不了了」。
最终,他被说动了,同意和我一起想办法撤出来。
-05-
赎罪与使命
两个月后,我解散了自己手下的 40 多个下线,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,协助警方抓获了组织中的几名 A 级别的头目。
离开传销组织后,我回到了鞍山,却不敢面对那些被自己骗过的亲戚朋友,每天躲在家中,闭门不出。为了发泄情绪,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,记录自己在传销组织中的经历,揭露它们的骗局。
令我意外的是,我写的这些文章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到我,说自己有亲人身陷传销组织,执迷不悟,希望我能帮他们把家人给劝回来。
于是,抱着赎罪的心态,或者说是一种「被需要」的使命感,我开始反传销。
在那个时期,我一般会通过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,去劝告受害者远离传销。对于那些被洗脑的人来说,只有「同行」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。当他们发现我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多的了解,甚至了解得比他们还要多,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好奇,希望从我这里了解「上面」到底是什么情况,进而一步一步醒悟过来。
如今回想起来,那段时间,我完全是凭着一腔激情在全国各地反传销,没有收入,也没有团队。有的时候,我连路费都拿不出来,只能靠反传销群里的群友们资助,才能勉强支撑。
-06-
反传销,就是反洗脑
2009 年 1 月,我和全国各地的十几名反传销人士聚集在河南新乡,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。为了扩大影响力,两个月后,我们搬到了北京,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工作室,用来接待那些需要被解救的传销受害者。在当时的设想中,我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像「戒毒所」一样的「戒传所」。
这十年来,每个月都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而来,带着他们身陷传销的亲人找到我们。而我们则会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,找到有类似经验的志愿者和他们谈话,帮助他们脱离洗脑。
在我这些年的经验中,反传销的关键在于「反洗脑」。
简单来说,传销组织的厉害之处,就是用一套成体系的谎言和假象,去营造神秘感,让受害者迷失在环境所带来的心理暗示中,陷入狂热,接受洗脑。而反传销要做的,就是把神秘感戳破,用事实和真相来给受害者重新洗一遍脑。
「
反传销中心」
和很多人设想的不同,在我们接触的受害者中,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对于这类群体,他们往往很难被洗脑,但一旦被洗脑,也很难被说服。
有一次,我们这里来了一位研究生在读的女生。面对我们的劝说,她完全充耳不闻,自以为接受过高等教育,绝对不可能受骗。被家人带来后,她在我们这里绝食了三天,不听,不看,也不说话。
三天后,我不得不从山东调来了一位「外援」。这位「外援」五十多岁,是一位教师。几年前,他被朋友骗到了广西的一个传销组织,最终却说服朋友一起离开了组织。后来,为了挽救更多的人,他加入了我们,偶尔会趁着假期来北京帮助我们做解救工作。
当天晚上,他就和那个女孩聊了个通宵,最终说动了她。事后,女孩告诉我们,她之所以会动摇,一方面是被这位长途跋涉而来的长辈打动了;更重要的是,那位老师见识广博,能把话说到她的心里去,而一旦消除了抵触心理,她很快便接受了我们向她展示的事实。用她的话来说,在此之前,「你们讲的都有道理,我都听进去了,但我始终不愿意相信,我明明学历不差,竟然也会受骗。」「传销课堂」给传销人员进行劝说反洗脑
就在前几天,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难劝的受害者。在加入传销组织前,她曾是一个成功的经商者。这两年,由于生意发展不佳,她被一个朋友骗到了山东青岛,做一个民间小额互助理财的的投资项目。一年多以来,她投资了十几万,对家人的劝告不闻不问,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狂热。
不久前,她的丈夫以自己要来北京看病为由,把她骗来北京,送到了我们中心。当她意识到自己「受骗」了的时候,立刻就产生了抵触心理,在现场闹得鸡犬不宁,还和丈夫打了起来。
她们一家人在我们这里住了好些天。在此期间,我给她详细分析了她所做的项目究竟有哪些漏洞和谎言。但无论如何,她都不肯放弃传销。毕竟,一旦放弃,她投下去的十几万就拿不回来了。
最终,她没有败给我们的理性分析,而是败给了儿子的亲情攻势——到了第三天,他的儿子给母亲跪了下来,求她回家,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反反复复的拉扯中,她决定放弃自己的坚持,跟着家人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去。
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离开的背景,我有些感慨。反传销这件事,拯救的往往不是某个个人,而是他们的家庭。
-07-
能救一个是一个
如今,我们的反传销团队已经有了三十多名全职工作人员。我们的传销解救服务一般会收取两到三千的费用,用来维持团队的正常运转。
但不得不承认,我们民间反传力量是很薄弱的,全国各地致力于此的人加起来,恐怕也不会超过一百个。相比于庞大的传销群体,我们的力量只是杯水车薪。与此同时,当下的传销团伙不仅越来越猖獗,他们的模式也在不停地升级换代,主流运行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异地传销,而是逐渐发展为网络传销。 无论是对我们,还是对警方来说,打击传销的难度都是越来越大的。
对我来说,这将是一份终身的事业。无论前景如何,我能救一个,就是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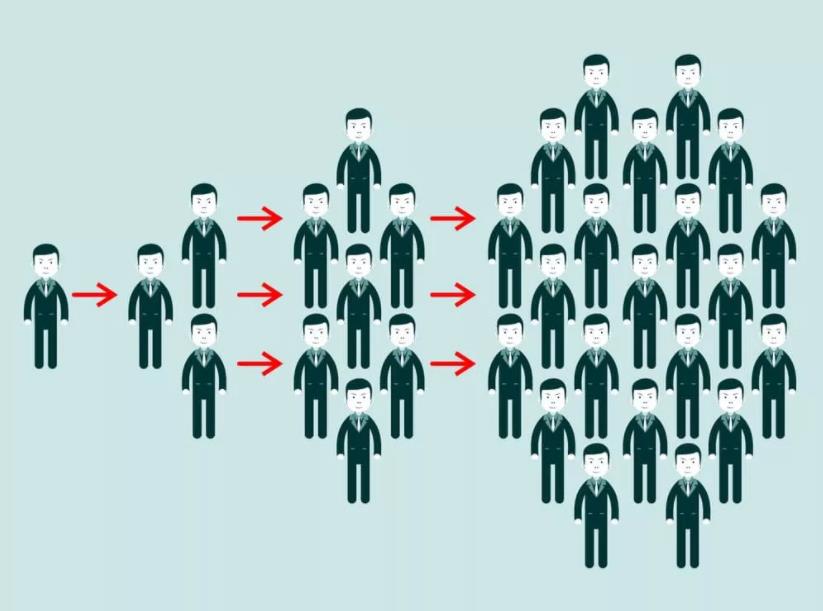 -01-
-01-